腸道微生物組生態學
作者:紮克·安德魯德博士
本文介紹了腸道微生物組的基本生態學。 強調腸道微生物組的三個最實質性的好處,包括防止腦腸道微生物組化學物質
在我們的每個大腸中都生活著數萬億種微生物,這些微生物共同構成了我們健康中心的支援器官,稱為腸道微生物組。我們的腸道擁有最高密度的微生物,主要屬於細菌,但也屬於地球上任何生物群落或微生物組的真菌、古細菌和原生生物。超過5,000種不同種類的微生物物種重約2公斤或4.4磅 – 幾乎是我們大腦的兩倍 – 生活在我們的消化道內(Bäckhed等人,2005年;塞基羅夫等人,2009年;Sender et al 2016)。我們自己是細菌和人類的平等部分,我們微生物組中的細胞數量等於我們自己的細胞。
此外,如果我們調查負責該活動的基因,我們的腸道微生物群可能表達的基因≥我們自己的基因組的 100 倍,具有 330 萬個獨特的編碼基因,而我們整個人類基因組中的 23,000 個基因(Amon and Sanderson 2017)。
但是,在我們關注由於腸道微生物組遺傳多樣性而導致的許多多樣化和基本功能之前,我們需要討論消化道的生態學。 在基礎水準上,我們的消化發生在一個生態系統中,在這個生態系統中,生物(即我們的胃腸道,腸道微生物組)和非生物成分(即我們吃的食物)相互作用。 讓我們分解這些元件中的每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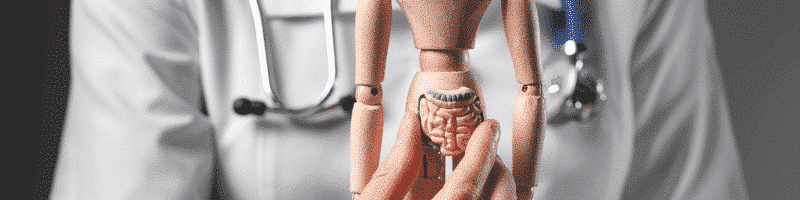
消化道
雖然營養物質在吸收部位附近最高,但胃和小腸含有相對較少的微生物。 由於胃內容物的低pH值,膽鹽的微生物毒性以及消化物的相對快速流動,這些區域的微生物數量受到限制。 超過90%的消化發生在這些氧氣濃度相對較高的部位(Rinninella等人,2019年)。
相比之下,胃腸道遠端的大腸保留並繼續消化食物的時間是小腸的六倍,並在低氧環境中為我們提供多種其他服務。 在腸道內,腸上皮細胞形成胃腸道的一層或管腔表面或內壁。 該層有兩個主要功能:將有用物質吸收到體內和限制有害物質或微生物的進入。 為了正確執行這些任務,腸上皮細胞在身體和腸道之間產生腸粘膜的腸粘膜屏障,防止管腔內容物不受控制地轉移到體內,並將細菌容納在大腸中。
腸道微生物組
我們超過 99% 的腸道微生物組位於大腸中,細菌要麼是粘膜相關細菌,由於靠近上皮而對我們的免疫和代謝健康產生長期影響(Juge 2022),要麼是更多短暫的自由生活細菌每天通過我們的大腸。 佔據粘膜層壁龕的細菌是我們大腸的真正居民,而自由生活的細菌只是在我們的腸道中“搭便車”。 在大腸結腸中,低氧環境,您會發現厭氧細菌以細菌門為主,桿菌門(以前稱為厚壁菌門)、擬桿菌門、放線菌門和偽菌門(以前稱為變形桿菌門)和屬 擬桿菌、梭狀芽胞桿菌、糞桿菌、真桿菌、瘤胃球菌、消化球菌、消化球菌和 雙歧桿菌 (Rinninella 等人,2019 年)。 其他屬如 埃希氏 菌和 乳酸桿菌 的存在程度較小。
您的食物
最終,我們糞便幹品質的60%是腸道微生物組細菌。 我們腸道中大量細菌的碳和能量需求由幾個來源滿足:複雜的膳食多酚、可消化纖維、其他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逃脫消化的脂肪、宿主分泌物(粘蛋白)的成分和脫落的上皮細胞。 大腸中細菌多樣性的驚人程度表明,許多生態位不僅由我們自己的生理學創造,而且通過複雜食物網的發展而產生,其中一種細菌的副產品可能成為其他細菌的基質(Walter 2008)。 我們的飲食決定了有助於使我們的微生物組多樣化的食物類型。
腸道微生物組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健康益處,本文將重點介紹三種益處——增強我們的免疫系統、產生維生素/對抗毒素以及產生影響我們心理健康的神經遞質。

免疫增強
健康的腸道微生物組可以極大地增強您的免疫系統,或保護我們的身體免受感染的器官、細胞和蛋白質的複雜網路。 我們大腸的細菌居民改變了腸道化學,完全佔據了腸道的空間,並分泌排除潛在病原體的抗菌蛋白。 我們腸道中的細菌通過發酵代謝食物併產生短鏈脂肪酸 (SCFA),如乙酸、丁酸和丙酸。 這些 SCFA 通過降低胃 pH 值和抑制艱難梭菌等有害病原體的生長來增強宿主抗菌免疫反應(Ouyang 等人,2022 年)。艱難梭菌是一種機會性腹瀉病原體,導致抗生素治療通常在全球範圍內引起的嚴重發病率和死亡率(Gregory 等人,2021年)。
支援增加SCFA水準的食物是膳食多酚,低聚果糖和難以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和纖維,如菊粉,抗性澱粉,樹膠和果膠。 此外,我們腸道微生物組中的許多常駐和暫態細菌會產生少量稱為細菌素的抗菌分子(例如,小黴素、腸球菌素和葡萄球菌素),這些分子具有消除特定定植病原體的能力(Heilbronner 等人,2021年)。 SCFA還有助於維持腸上皮細胞的完整性。
微生物的不平衡或粘膜屏障的破壞在稱為生態失調的過程中增加了上皮的腸道通透性。 不幸的是,腸道生態失調會加劇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類風濕性關節炎、多發性硬化症和乳糜瀉(Chang 和 Choi 2023;陳和維泰塔 2021)。 健康的腸道微生物群極大地有助於維持體內的體內平衡,支援免疫系統正常運作。
維生素和毒素
對我們的健康至關重要的特定維生素僅在我們的腸道微生物群中產生。 大多數維生素必須從外部來源提供。 維生素存在於各種食物中,但這意味著由於飲食不良,可能會出現維生素缺乏症。
出乎意料的是,我們的腸道微生物組可能會 從頭 合成維生素(從一開始就),尤其是 30% 以上的維生素 K 和 B 族維生素,如核黃素、煙酸和鈷胺素(Nysten 和 Dijick 2023)。 維生素 K 是骨骼、認知和心臟健康所必需的,維生素 B 群是維持整體健康所必需的,會影響能量水平、大腦功能和細胞代謝。
維生素對我們的健康至關重要,但其他化學物質對我們極其有害。 我們一直受到異生素(即通常不存在於生物體環境中的化學物質)的轟炸,從人為產生的污染到食品添加劑和殺蟲劑。 如果沒有我們的腸道微生物組代謝,許多異生素會達到毒性濃度(Croom 2012)。 由於遺傳多樣性,健康的腸道具有強大的代謝能力,可以生物轉化無數的異生素,遠遠超過我們自己的代謝潛力(Dikeocha 等人,2022 年;阿卜杜勒薩拉姆等人,2020 年)。
腸腦連接
您的大腦和腸道微生物組通過數百萬個神經細胞進行連續對話。 腸腦連接是生活在胃腸道中的細菌和中樞神經系統之間發生的生化信號。 生化信號由神經遞質(Reynoso-Garcia 等人,2022 年)引發,如 SCFA(Obata 和 Pachnis 2016)、5-羥色胺(5-HT,血清素)、γ-氨基丁酸(GABA;Pokusaeva等人,2017年)和皮質醇等激素(Valles-Colomer等人,2019年)。 腸道和大腦一起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腦部疾病的情緒、認知和病理生理學。
例如,我們95%的神經遞質血清素在我們的腸道中產生,它調節情緒(即情緒、睡眠、消化、噁心、癒合、骨骼健康、血液凝固和;特裡和馬戈利斯 2017)。 抑鬱症等其他神經精神疾病也與腸道生態失調有關。 一般來說,桿菌細菌的減少導致患有抑鬱症的SCFA下降,影響腸道屏障(Huang等人,2018)。 此外,抑鬱症中的雙歧桿菌水準也降低了,長雙歧桿菌和短雙歧桿菌等益生菌物種的重新引入減少了抑鬱行為,並增加了 5-羥色氨酸和丁酸鹽的分泌(Tian 等人,2019 年)。
最終,當我們有一種直覺,肚子里的蝴蝶,或者我們相信我們的腸道時,我們正在傾聽,部分,你的腸道微生物組和大腦之間的串擾。
與我們的腸道微生物群一起,我們形成了一個「超級有機體」。。 我們彼此依賴。 我們的腸道微生物組擁有數萬億個細胞、數千種不同的物種和相對無限的基因功能,它們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著我們大大低估的基本日常功能。 我們需要欣賞和培育我們的微生物群,以便我們可以充分受益於我們的健康中心。

作者簡介
Zach Aanderud擁有博士學位,是楊百翰大學微生物生態學和生物地球化學教授。 他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出生和長大,並在楊百翰大學、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和密歇根州立大學接受教育。
引用
Abdelsalam NA 等人 (2020) 毒理微生物組學:人類微生物組與藥物、飲食和環境異生素。 前藥理 11. DOI: 10.3389/fphar.2020.00390
Amon P和Sanderson I (2017) 什麼是微生物組。 Arch Dis Child Educ Practiceact Ed 102:258-261。 DOI: 10.1136/archdischild-2016-311643
Bäckhed F等人(2005)人體腸道中的宿主細菌共生。 科學 307:1915-20。 DOI: 10.1126/science.1104816
Chang S 和 Choi Y (2023) 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腸道生態失調:與死亡率的關聯。 前細胞感染微生物 31。 DOI: 10.3389/fcimb.2023.1157918
Chen J 和 Vitetta L (2021) 乳糜瀉的腸道生態失調:減少布圖酸鹽的產生可能會促進疾病的發作。 PNAS 118:41 e2113655118。 DOI: 10.1073/pnas.2113655118
Croom E (2012) 人類環境異生生物的代謝。 分子生物學進展翻譯科學 112:31-88。 DOI: 10.1016/B978-0-12-415813-9.00003-9
Dikeocha IJ 等人 (2022) 藥物微生物組學:腸道微生物群對藥物和異生代謝的影響。 法西伯書 36:6。 DOI: 10.1096/fj.202101986R
格雷戈里·AL,彭辛格 DA,赫里科維安 AJ (2021) 艱難梭菌 發病機制的短鏈脂肪酸中心觀點。 公共科學圖書館病理17:10 e1009959。 DOI 10.1371/journal.ppat.1009959
Heilbronner S等人(2021)細菌素的微生物組塑造作用。 自然評論 微生物學 19:726-739。 DOI: 10.1038/s41579-021-00569-w
黃瑩等(2018). 厚壁菌在重度抑鬱症患者的腸道微生物群中的可能關聯。 神經精神病治療 14:3329-3337。 DOI: 10.2147/NDT.S188340
Juge N (2022) 粘膜相關腸道微生物群與人類疾病之間的關係。 生化學報 Trans 50(5):1225–1236。 DOI: 10.1042/BST20201201
Knudsen JK 等人 (2021) 將抑鬱症患者或健康個體的糞便微生物群移植到大鼠體內,調節與情緒相關的行為。 科學代表 11:21869。 DOI: 10.1038/s41598-021-01248-9
LeBlanc等人(2013)細菌作為宿主的維生素供應商:腸道微生物群的觀點。 當前意見生物技術24 :2。 DOI: 10.1016/j.copbio.2012.08.005
Obata Y和Pachnis V(2016)微生物群和免疫系統對腸道神經系統發育和組織的影響。 胃腸病學 151:836-844。 DOI: 10.1053/j.gastro.2016.07.044
歐陽 Z 等人 (2021) 短鏈脂肪酸在 艱難梭菌 感染中的作用:綜述。 厭氧菌 75:102585 DOI:10.1016/j.厭氧菌.2022.102585
Pokusaeva K, et al (2017). 產生GABA的 齒狀雙歧桿菌 調節腸道中的內臟敏感性。 神經胃腸運動 29:e12904。 DOI: 10.1111/nmo.12904
雷諾索-加西亞等人 (2022) 人類微生物組完整指南:身體生態位、傳播、發育、生態失調和恢復。 前系統生物 2. DOI: 10.3389/fsysb.2022.951403
林尼內拉 E 等人 (2019). 健康的腸道微生物群組成是什麼? 跨越年齡、環境、飲食和疾病的不斷變化的生態系統。 微生物 7:E14。 DOI: 10.3390/微生物 7010014
Savage DC (1977) 胃腸道微生物生態學。 微生物學年鑒 31:107-33。 DOI: 10.1146/annurev.mi.31.100177.000543
Sekirov I,Russell SL,Antunes LC,Finlay BB(2019)健康和疾病中的腸道微生物群。 生理學。 轉速。 90:859–904. DOI:10.1152/physrev.00045.2009。
Sender等人(2016)對體內人類和細菌細胞數量的修訂估計。 公共科學圖書館生物學 14:e1002533。 DOI: 10.1371/journal.pbio.1002533
Valles-Colomer, M., Falony, G., Darzi, Y., Tigchelaar, E. F., Wang, J., Tito, R. Y., et al. (2019). 人類腸道微生物群在生活質量和抑鬱症中的神經活性潛力。 納特。 微生物。 4, 623–632. DOI:10.1038/s41564-018-0337-x
Terry N和Margolis KG(2017)調節胃腸道的血清素能機制:實驗證據和治療相關性。 手布實驗藥理學 239:319-342。 DOI: 10.1007/164_2016_103
Tian P等人(2019)攝入長 雙歧桿菌 亞種 嬰兒 菌株CCFM687通過重塑腸道微生物群來調節慢性應激誘導的抑鬱小鼠的情緒行為和中樞BDNF途徑。 食品功能 10:7588–7598。 DOI: 10.1039/c9fo01630a
